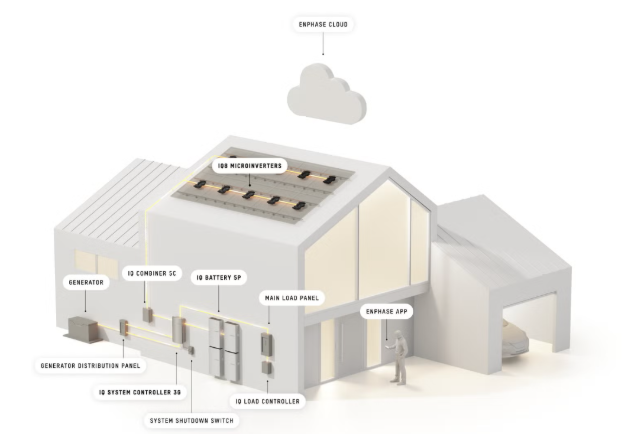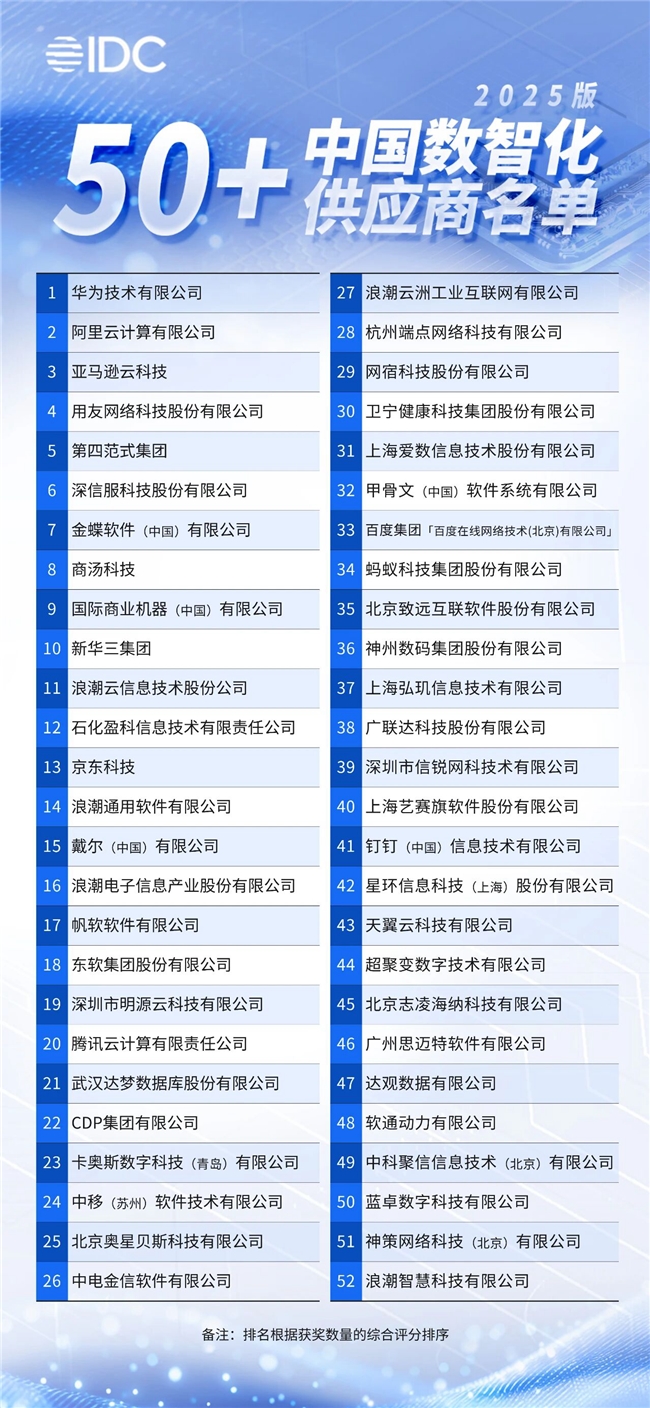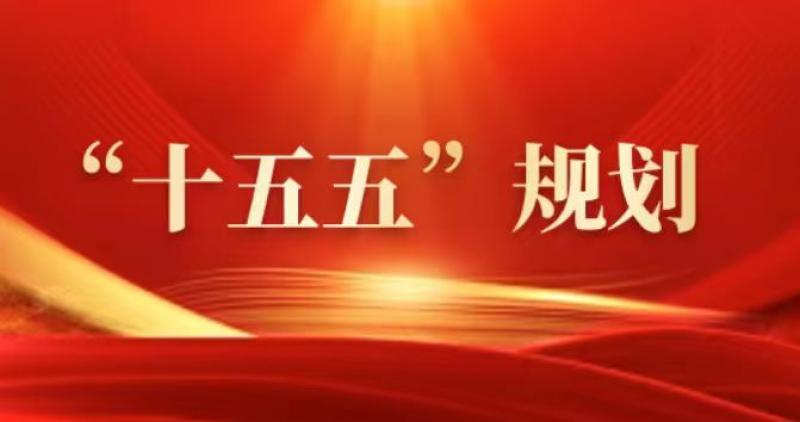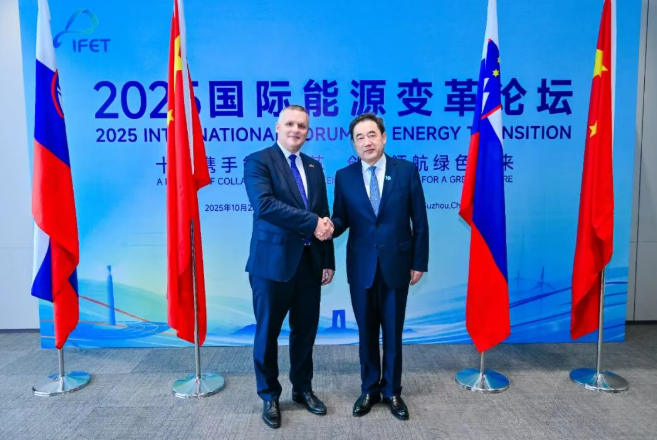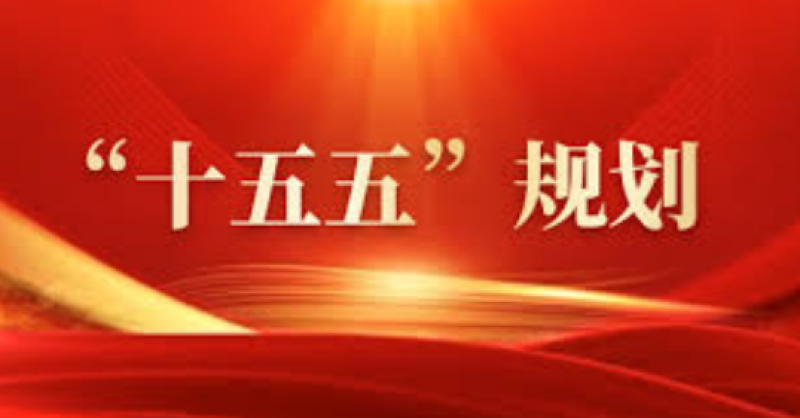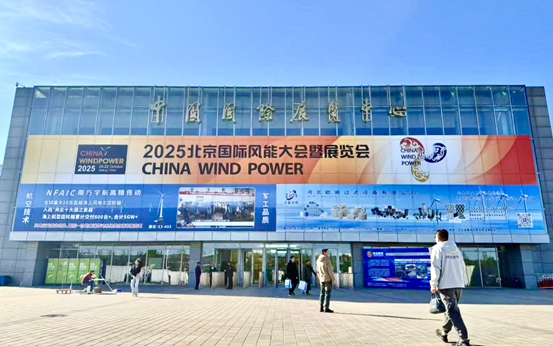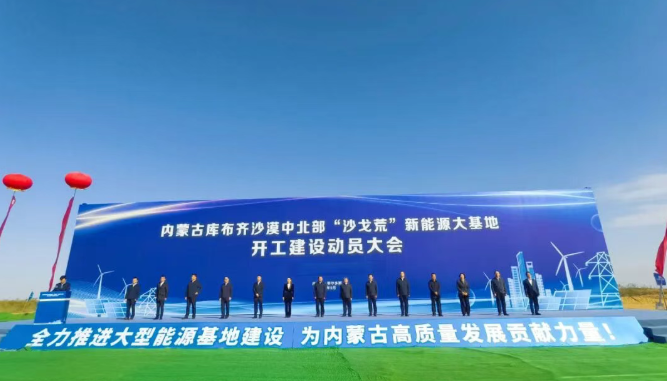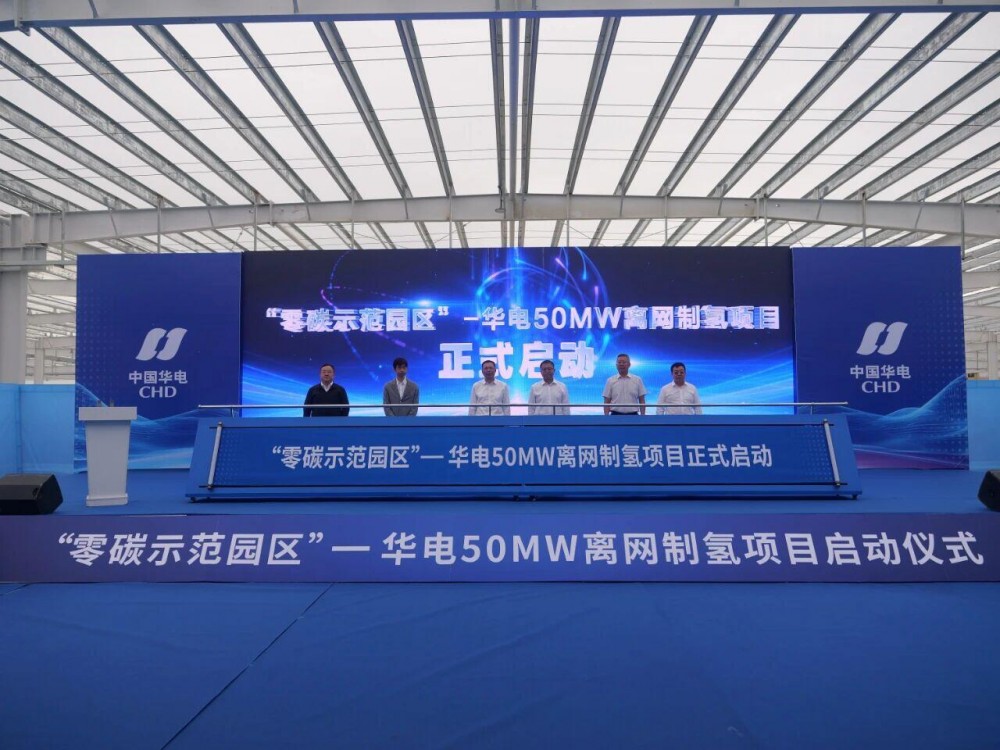據(jù)日本經(jīng)濟(jì)新聞4月13日消息,日本政府當(dāng)天舉行內(nèi)閣會(huì)議,正式?jīng)Q定向海洋排放福島核電站含有對(duì)海洋環(huán)境等有害的核廢水。
這一決定意味著東京電力公司(下稱(chēng)“東電”)將獲準(zhǔn)在兩年內(nèi)啟動(dòng)核污水的排放工作。這些仍具有放射性的污水是十年前福島核泄漏事故之后用來(lái)冷卻融毀受損的反應(yīng)堆而不斷產(chǎn)生的。
此前相關(guān)消息一出,立即引發(fā)了日本國(guó)內(nèi)和國(guó)際上的強(qiáng)烈反對(duì)。而事故背后的“始作俑者”東電,卻在3月25日就柏崎刈羽核電站發(fā)生安全違規(guī)情況道歉后,就靜悄悄地沒(méi)再作聲。

東電負(fù)責(zé)人向福島災(zāi)民下跪道歉。
如果沒(méi)有3·11東日本大地震和那一場(chǎng)海嘯,福島核事故是否就不會(huì)發(fā)生?
隱患其實(shí)早已埋下。
在福島核事故前,日本核電產(chǎn)業(yè)就已存在著嚴(yán)重的不透明性。這種不透明的背后,隱藏著一張錯(cuò)綜復(fù)雜的龐大利益網(wǎng)。
而這一切,是被一名通用公司的日裔美籍高級(jí)工程師——菅岡啟所揭露的。
2000年,正為通用公司在福島第一核電工廠進(jìn)行外包工程的菅岡啟,發(fā)現(xiàn)站內(nèi)一臺(tái)蒸汽干燥器出現(xiàn)了裂縫,對(duì)核電站的安全造成重大隱患。在將該情況上報(bào)給東電后,菅岡啟卻收到了東電“刪除所有相關(guān)證據(jù)和信息”的指示。在一段時(shí)間的思想斗爭(zhēng)后,菅岡啟決定直接將視頻證據(jù)發(fā)給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下稱(chēng)NISA)。
然而,NISA并沒(méi)有遣派調(diào)查員前往第一核電工廠,而僅是通知東電進(jìn)行自我審查,并對(duì)設(shè)備問(wèn)題“作出合適的解決”。與此同時(shí),雖然當(dāng)時(shí)日本已立法保護(hù)“吹哨人”,NISA還是將菅岡啟的信息提供給了東電,導(dǎo)致其被解雇,并在日后不斷受到東電威脅。
這一事件將東電推上了輿論的風(fēng)口浪尖。
東電2007年向日本經(jīng)濟(jì)產(chǎn)業(yè)省提交的調(diào)查報(bào)告顯示,自1977年以來(lái),東電對(duì)下屬的福島第一、第二,以及柏崎刈羽核電站的13座反應(yīng)堆總計(jì)199次定期檢查中,存在篡改數(shù)據(jù)和隱瞞安全隱患的行為。
東電在處理核泄漏問(wèn)題上的應(yīng)急機(jī)制不斷遭到各界質(zhì)疑,在輿論的不斷追問(wèn)下,一個(gè)被日媒稱(chēng)為“原子能村”的封閉利益集團(tuán)逐漸浮出水面。
“原子能村” 由官、商、學(xué)三方組成。“官”指的是以經(jīng)濟(jì)產(chǎn)業(yè)省資源能源廳和NISA組成的官僚集團(tuán);“商”指的是以東電為首的電力企業(yè)和日立、東芝等核電設(shè)備商;“學(xué)”指的是分布在原子能源委員會(huì)和其他核能研究開(kāi)發(fā)機(jī)構(gòu)的專(zhuān)家學(xué)者。
本應(yīng)起到相互監(jiān)督、牽制的三個(gè)構(gòu)成方,卻在推進(jìn)核電發(fā)展過(guò)程中,成為了一個(gè)相互交換承包合同、提供高薪工作,以及為核電推進(jìn)提供資金、政治和立法支持的利益集團(tuán)。
示威者高舉標(biāo)語(yǔ),譴責(zé)東京電力公司(TEPCO)。
從1959年至2010年,至少有四名政府監(jiān)管部門(mén)的高層官員曾“天降”至東電擔(dān)任副董事長(zhǎng)的職務(wù)。此外,在經(jīng)濟(jì)產(chǎn)業(yè)省資源能源廳和NISA工作的官員,在職業(yè)生涯中常在監(jiān)管和宣傳崗位間來(lái)回調(diào)換。
學(xué)術(shù)界也不例外。在日本,關(guān)于核電的學(xué)術(shù)研究都是由政府撥款資助的,因此,對(duì)核電持懷疑態(tài)度的學(xué)者往往無(wú)法得到科研資金。此外,由于NISA普遍缺乏專(zhuān)業(yè)知識(shí),其在起草核電相關(guān)法規(guī)時(shí)往往會(huì)尋求學(xué)術(shù)界的支持,而此時(shí)其也只會(huì)轉(zhuǎn)向支持核電發(fā)展的學(xué)者和專(zhuān)家,導(dǎo)致相關(guān)法規(guī)往往并不能起到有力的監(jiān)管作用。
“原子能村”的存在,解釋了為什么東電能在屢屢爆出監(jiān)管不力和故意隱瞞隱患的丑聞的“騷操作”下,還能躲過(guò)政府制裁,并最終導(dǎo)致了福島核事故的悲慘結(jié)局。
2011年3月11日23時(shí)許,福島第一核電廠完全失去了用電,這意味著沒(méi)有足夠的冷卻水供應(yīng)。隨之而來(lái)的,是一連串多米諾骨牌反應(yīng)——反應(yīng)堆內(nèi)的燃料棒的衰變熱無(wú)法導(dǎo)出,導(dǎo)致堆芯內(nèi)的冷卻水溫度不斷升高,最終沸騰。高溫高壓的蒸汽開(kāi)始突破堆芯回路內(nèi)一些薄弱環(huán)節(jié),開(kāi)始向廠房?jī)?nèi)泄漏。而由于冷卻水變成蒸氣從堆芯內(nèi)散逸出去,使得燃料棒開(kāi)始裸露在空氣中,徹底失去了冷卻。
燃料棒失去冷卻的那一刻,災(zāi)難開(kāi)始了。巨大的熱量將燃料棒熔化后,又熔化了包裹著燃料的鋯合金。高溫的鋯合金和水蒸氣發(fā)生反應(yīng),產(chǎn)生了大量氫氣,氫氣不斷從毀壞的反應(yīng)堆溢出,在廠房屋頂聚集。同時(shí),失去包裹的燃料中,大量的放射性元素在水蒸氣的裹挾下向外泄漏。
東電2011年6月21日關(guān)于福島核電站1、2號(hào)反應(yīng)堆氫爆炸事故調(diào)查推測(cè)報(bào)告:高溫/高壓造成密封功能降低,導(dǎo)致氫氣泄露(氣體通過(guò)安全殼貫穿部位泄露,引發(fā)爆炸)。
即便這樣,東電仍試圖隱瞞實(shí)情。甚至在福島1號(hào)機(jī)組廠房爆炸后,內(nèi)部通知也只以“出現(xiàn)白煙和巨響,正在調(diào)查中”來(lái)表述,更別說(shuō)在第一時(shí)間把消息向日本當(dāng)局匯報(bào)了。
據(jù)調(diào)查福島核事故的日本第三方檢證委員事后出臺(tái)的報(bào)告指出,事故發(fā)生時(shí)東電社長(zhǎng)清水正孝指示不要對(duì)外使用“堆芯熔化”一詞。報(bào)告還推斷,清水正孝當(dāng)時(shí)“領(lǐng)會(huì)”了首相官邸的要求,即需要“慎重”承認(rèn)堆芯熔化。
2011年3月14日拍攝的衛(wèi)星照片: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3號(hào)反應(yīng)堆爆炸后冒起濃煙,左下為1號(hào)反應(yīng)堆。
眼看已經(jīng)火燒眉毛,有技術(shù)專(zhuān)家提出了一個(gè)“沒(méi)辦法的辦法”——使用含高硼酸的海水作為冷卻水來(lái)冷卻反應(yīng)堆。然而,硼元素會(huì)腐蝕反應(yīng)堆,注入海水可能意味著“廢堆”。
東電無(wú)一人敢拍板作決定。
這是因?yàn)椋⑺剂颗c整個(gè)電力系統(tǒng)的資產(chǎn)盈利狀況相關(guān)。2007年,東京電力面臨56%產(chǎn)能關(guān)停,凈收益預(yù)期下調(diào)79%的處境。公司在2007和2008財(cái)政年度凈虧損,2009財(cái)年?duì)I業(yè)利潤(rùn)僅為2006財(cái)年的一半。東京電力已有的核能資產(chǎn)維護(hù)費(fèi)用不低,若稍有停產(chǎn)即會(huì)造成負(fù)收益。
此外,東電背后還和財(cái)團(tuán)家族、政府官員之間已經(jīng)存在“利益勾連”。事實(shí)上,日本核能發(fā)展領(lǐng)域一直存在政府參與。日本發(fā)展銀行是東京電力和核能發(fā)電企業(yè)最大的貸款來(lái)源,截至事故發(fā)生前的上一財(cái)政年度,提供的長(zhǎng)期貸款達(dá)3510億日元。而在東電十大股東中,多是日本排名前列的信托銀行和保險(xiǎn)業(yè)巨頭,其背后不乏三菱、住友等大財(cái)團(tuán)的身影,其持股份額達(dá)35%左右。
為了力保資產(chǎn),東電錯(cuò)過(guò)了最佳應(yīng)對(duì)時(shí)機(jī)。直到3月12日15時(shí)30分左右,1號(hào)機(jī)組發(fā)生了爆炸,時(shí)任日本首相菅直人18時(shí)許下令后,東電才從附近海岸取水,用于冷卻1號(hào)機(jī)組。而此時(shí)距離海嘯發(fā)生,已經(jīng)過(guò)去了整整28小時(shí)。東京電力直到3月13日才開(kāi)始用海水冷卻其他反應(yīng)堆。
身著防護(hù)服的東電工人。
即便如此,東電依舊沒(méi)有吸取教訓(xùn)。事故發(fā)生10年后,遲報(bào)瞞報(bào)的一幕再次上演。2021年2月13日晚,福島縣附近海域發(fā)生7.3級(jí)強(qiáng)震。而地震發(fā)生一周后,東電才表示,福島核電站兩臺(tái)地震監(jiān)測(cè)器損壞半年沒(méi)有修理,未能獲得地震數(shù)據(jù);2月25日,東電披露,福島核電站53個(gè)核污水罐因強(qiáng)震發(fā)生位移……
2013年8月19日,東電對(duì)外發(fā)布消息,承認(rèn)福島第一核電站地上儲(chǔ)罐發(fā)生泄漏,并稱(chēng)泄露量數(shù)值為至少120公升。但很快東電就將這個(gè)數(shù)值調(diào)整為約300噸,并且沒(méi)有否認(rèn)污水流入太平洋的可能性。
但東電其實(shí)原本有機(jī)會(huì)將這次損失降低:早在當(dāng)年7月9日,在泄漏處附近檢查工作的職員就在日常輻射檢查中被檢出輻射值上升,但并沒(méi)有受到重視。
在日本原子力規(guī)制委員會(huì)后續(xù)公布的調(diào)查中也表明,東電在一天兩次的儲(chǔ)水罐檢查巡邏過(guò)程中,都沒(méi)有留下相關(guān)的記錄,更沒(méi)有及時(shí)發(fā)現(xiàn)泄漏的相關(guān)跡象。“每天兩次在儲(chǔ)水罐區(qū)的巡邏被指幾乎形同散步”,東電在儲(chǔ)水罐管理上粗糙的做法是導(dǎo)致核污水大量外泄的原因之一。
然而,這樣嚴(yán)重的核污水泄漏事件,在福島發(fā)生了不止一次。
“儲(chǔ)水罐出現(xiàn)裂縫”“本應(yīng)關(guān)閉的閥門(mén)無(wú)故處于開(kāi)放狀態(tài)導(dǎo)致儲(chǔ)水罐泄漏”“高濃度核污水被誤送至其他廠房”“受大雨影響污水溢出”......
實(shí)在有點(diǎn)難想象,這些竟然都會(huì)和一家本該“管理森嚴(yán)”的核電站扯上關(guān)系。但在東電管理下的福島,這些都真真切切發(fā)生過(guò)。
除了多次發(fā)生的污水泄漏事故,東電屢次“自己打臉自己”的行為,也讓其長(zhǎng)期備受質(zhì)疑。
根據(jù)東電自2013年來(lái)的官方說(shuō)法,其“多核素去除設(shè)備”(ALPS)技術(shù)能將放射性物質(zhì)含量降至“低于容許排放的水平”。然而2018年9月,東電才第一次對(duì)外承認(rèn),用于處理含有核污水的儲(chǔ)水罐中有1000個(gè)都未能將放射性物質(zhì)去除至低于法定標(biāo)準(zhǔn)值。
不僅如此,2018年10月17日,東電還曾對(duì)外發(fā)布消息,稱(chēng)自己向日本政府的小委員會(huì)匯報(bào)的,有關(guān)福島第一核電站核污水經(jīng)ALPS凈化后所含放射性物質(zhì)測(cè)定結(jié)果圖表有至少260處錯(cuò)誤,原因是原始數(shù)據(jù)制成圖表時(shí)發(fā)生了放射性物質(zhì)種類(lèi)歸錯(cuò)或輸入錯(cuò)誤。18日,東電又透露,在對(duì)訂正數(shù)進(jìn)行詳查后發(fā)現(xiàn),實(shí)際錯(cuò)誤有1276處。
在日本政府基本決定將污水排入大海后,國(guó)際原子能機(jī)構(gòu)(IAEA)曾對(duì)外表示,支持將福島第一核電站蓄積的處理水排放入海,稱(chēng)其符合國(guó)際慣例。
然而,仍有不少科學(xué)環(huán)境組織對(duì)上述定論表示質(zhì)疑。鑒于東電在核事故處理上的種種“劣跡”,這家公司向國(guó)際原子能機(jī)構(gòu)提供的數(shù)據(jù)是否能保證“準(zhǔn)確無(wú)誤”?這次,東電靠得住嗎?